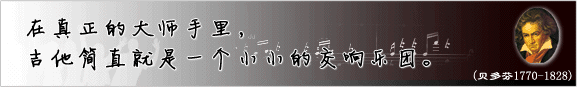|
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
《第一交响曲》
一些片断性的草稿表明,贝多芬在离开波恩之前就有志于创作交响曲了,但他正式动笔写作交响曲的时间稍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海顿的后期交响曲,还有莫扎特的同类作品被公认为典范之作,这些作品在每个方面都堪称完美和不可超越,没人相信交响音乐可以在古典主义的范型里达到第三座高峰。
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op.21)作于1799至1800年期间,这部“庄严的”交响曲(“庄严的”是此曲1801年初版时的标题)是由作曲家亲自指挥首演的,地点在维也纳皇家宫廷剧院。同时上演的还有七重奏(op.20)和他的一首钢琴协奏曲(不是《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op.15)就是《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op.19))。一位评论家在《大众音乐报》(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指出:“这部交响曲作为一部创作,充满了大量的技巧和丰富新奇的意念,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使用了太多的管乐器,这使得它听起来更像是写给管乐队,而不是给全体交响乐团的”(这评论也预示着,当时大量的交响乐团的编排或者说他们的演奏缺乏平衡)关于这部作品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的意见都介于欣赏和颂扬之间,1805年的《大众音乐报》称它是一部“宏伟而美妙的创作”;《历史袖珍手册》(Historisches Taschenbuch)提到它时,称之为“一部杰作,无愧于作曲家的创造力和音乐才能,它们都同样美好而卓越,不管是构思还是创作,都是那么清晰,那么秩序井然,令人愉快的旋律不绝如缕,还有丰盈而不过份的管弦乐配器,可以说,这部交响曲甚至完全可以与海顿和莫扎特的同类作品并肩而立”,
卡尔•马利亚•冯•韦伯有时会尖刻的批评贝多芬,然而也认为这部《第一交响曲》是“宏伟、明澈和热烈的”。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这部作品是一首“怪异之作”,这也是对作者后来一些作品的常见回应。
在这部C大调交响曲中,存在着对莫扎特,尤其是对于海顿的模仿,这是无可否认的。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作品的独创性和青春的活力:导入缓慢的引子(极缓慢的)的七和弦刚一露头,就显现出新的、不同寻常的东西,此外,末乐章的引人注目的缓慢开头,高度自信的结尾部也都是如此,这样的音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另一方面,托维指出,《第一交响曲》是“对十八世纪的告别”,真可谓一语中的。
贝多芬在这部作品和以后的创作中保持了对古典主义作曲原则的忠实,这些原则已经在海顿和莫扎特的创作中得到实施。这在开始就是明明白白的,在活泼、朝气蓬勃的快板(从第13到第32小节)的第一个主题群里,不同的粒子自然地组成单一的、规则的、成型的实体,从而,自由、易变的因素的分离发展为一种建筑结构,其中,自由与必然已不再是对立的了。(注意:管乐和弦乐结合成基本主题的方式,或者弦乐在第24小节,以既不可预知、又自然而然的方式出现在不谐和的C大调上都是显例)第一乐章尤富于旋律、配器、节奏上的创造,它们一起构成了结构的整体。在“稍快如歌的行板”中,洋溢着优雅、轻松的海顿精神,随后的小步舞曲首次在交响曲中以贝多芬式谐谑曲的面目出现,末乐章精神抖擞地结束了全曲。
《第一交响曲》的第一版题献给了皇家图书管理员,外交官和音乐爱好者格特弗里德(Gottfried),他与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关系很好,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他的住处组织演奏过巴赫、亨德尔的作品哩。
《第二交响曲》
贝多芬独特的个人化声音在《第二交响曲》(op.36)中来得更加真切,他的意念的热情,他的炽烈的理想主义呼之欲出。贝多芬于1801-1802年写出了他的《D大调交响曲》。这段时间,严重的个人危机——耳聋已经出现征兆,这些都记录在他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海利根施塔特是离维也纳不远的一个村庄,贝多芬在那里度过了1802年的夏季和初秋,在返回维也纳之前,交响曲已经完成。然而,这部作品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作品激情四溢,丝毫看不到心情沮丧的迹象。缓慢的引子已经表明贝多芬并没有放弃海顿和莫扎特对于乐队的编排布置,也没有抛弃古典主义原则。在此处或后来的作品中,也许存在一个悖论:贝多芬越是展示他自己,将他和海顿、莫扎特的音乐连接起来的精神就凸现得越清晰——在某种程度上,这基于他崇奉这样的原理,那就是结构的合理性一定表明其自身对于作曲家个体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第二交响曲》于1803年4月在维也纳剧院首次公演,音乐会上还包括《第一交响曲》,《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曲家担任独奏)和清唱剧《基督在橄榄山上》。关于这场演出,众说纷纭,对于贝多芬自己的演奏,评论认为“没有做到令听众完全满意”。《第一世界报》(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的评论家相信“和现在的这首D大调相比,《第一交响曲》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贯彻了自然而轻盈的感触,可是在《第二交响曲》中,对那些新鲜的、非凡的东西做出的回应更加表面化(不够自然)”。但又补充:“然而,不言而喻,两部作品都不缺少美感,这一点是显而易见而且非常突出的”。弗里德里克•罗歇里茨,这位著名的《大众音乐报》(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的编辑,态度鲜明地断言:“当如今大量时髦的曲子湮没无闻以后,《第二交响曲》仍将作为一部具有炽烈感情的作品存在下去。”在当时,对于不朽的作品和昙花一现的作品之间的美学差异已经被注意到,独特和不朽已经成为艺术作品的标记,这体现在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创作中,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正是抱持这样的信念来创作的。
长大的引子之后是活泼、朝气蓬勃的快板(allegro con brio),如同《第一交响曲》,在活泼、朝气蓬勃的快板中,贝多芬式的魅力以可察觉的,更为自信的姿态显现出来。重复的动机式的主题材料采取了胜利的、进行曲式的音调,由此开拓出对立力量的冲突,而音乐要素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却丝毫未损。慢乐章采用的是属调A大调,这是颇不寻常的。这个调性倾向于辉煌灿烂的效果。就音乐活力而论,它凌驾于《第一交响曲》的慢板之上,而它的视野也被音乐要素所具有的崇高的理想主义和连德勒舞曲的性格延展了。在兴奋的谐谑曲中,贝多芬的个性被表达得最清楚不过,在贝多芬的交响曲中,第一次出现了“谐谑曲”的标记,本来与谐谑曲无关的三声中部也是神来之笔。终曲乐章由一个摇摆音型的主题开始,然而节奏是坚定不移的,这事实上是释放那些相反冲动的某种方式,这冲动造就了壮丽而复杂的音乐构架,这是贝多芬第一个重要的交响曲终曲。此曲第一版的标题为“大交响曲”,它是题献给卡尔•冯•里西诺夫斯基王子(karl von Lichnowsky,1761-1814年)的,王子是莫扎特的朋友,也是当时贝多芬最亲近的朋友之一。
《第三交响曲》与《埃格蒙特序曲》
贝多芬的人生荣耀在1802年至1803年达到顶点,这个时期也标志着他生活的危机和转折。可以说明此点的第一个证据自于他那感人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1802年11月)。当时他已经有了耳聋的初期征兆。同时,不少材料表明,当时他的艺术理念也正发生改变。据车尼尔回忆,大约在1803年,他对他的朋友,小提琴家克鲁姆费尔茨说:“我认为我迄今为止的作品只是差强人意,从现在开始我要另辟蹊径。”更早以前(1802年11月),他对他的出版商描述钢琴变奏曲op.34和op.35“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创作的”。
相对于《第三交响曲》的终曲,号称“英雄”变奏曲的作品op.35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当然,它是完全独立的。理查德•瓦格纳描述这个主题是一个“最初的曲调”,事实上,它的确具有潜在的基本主题模型的品格,并成为《英雄交响曲》终曲乐章大幅度的交响性发展的基础,它实际上是向贝多芬曾经采用过的对面舞曲的回归。在芭蕾舞曲《普罗米修斯的生民》OP.43(1800—1801 年)中,对面舞曲也是出现于最后乐章。其实《英雄交响曲》终曲本身的确堪称一个理想化的、普罗米修斯般的舞曲乐章。
交响曲的四个乐章都表明,作者正在探索新的领域,这个领域充满了崇高、雄浑的情绪氛围,正如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些作品,诸如《克鲁采奏鸣曲》(op.47)、《华德斯坦奏鸣曲》(op.53)、《热情奏鸣曲》(op.57)以及《拉祖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op.59)都显示了与《英雄交响曲》的“必然联系”。
《第三交响曲》(1806年)最初版本的全称是“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个伟人而作”。贝多芬在1803年就完成了交响曲的主体部分,当时打算命名为“波拿巴”。在那个年代,拿破仑已经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他和黑格尔和歌德一起,作为伟大人格的化身,注定要引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并且,在通常意义上,是要去实现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的。1804年4月,身在维也纳的贝多芬获悉拿破仑称帝的消息,他愤怒地涂去了拿破仑的名字,指责他“只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现在他就要践踏一切人的权利,成为暴君了!”
在贝多芬的心目中,英雄的概念与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行动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即使有人说拿破仑这个人促成了这部交响曲,我们也不能确信在作曲家心中存在一个确定的历史人物(作为音乐的原型),更不用说存在任何实际的或想象中的“英雄的生涯”了。我们从《英雄交响曲》中看到的是英雄主义的意念激发起来的冲动所造成的交响曲样式的生成,是内涵和外延的崇高伟大:这两者都是贝多芬音乐的特点。
由“崇高”的E大调写成的《第三交响曲》,以天然的维度打破了一切既有的评判标准。可以肯定的是,主题和节奏的冲突体现出的性格里具有一种不可遏止的英雄般的锐气,主要主题凭着这股锐气展现自身并获得其最终的形式。(第一乐章起始处坚定的和弦和接下来乐思的丰富多姿都是相当独特的。)音乐的结构完全没有受到主题乐思爆炸性力量的威胁,实际上,这个乐章的结构相当严格和紧凑。
葬礼进行曲-极柔板是交响曲的中心,采用的是这一体裁惯用的C小调,这个乐章和钢琴奏鸣曲op.26中的葬礼进行曲形成对照,不必将这里的葬礼和某个实际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它将听众带进怀念的情绪中,感人至深,进行曲的主题在乐章结尾分解为碎片。狂放不羁的圆圈舞构成的谐谑曲成为终曲变奏延伸出来的引子。在终曲乐章,贝多芬借着以自然的冲动为特征的对面舞主题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其中,幽暗的调子被一扫而空。
《英雄交响曲》于1805年4月7日第一次公演,此前,这首交响乐曾经献给洛伯科维茨王子并在他的宫殿里演奏过。当时的许多听众无法理解音乐中的“庄严,大胆的乐思”,反而觉得音乐不够“轻松,明瞭与和谐”,这是不奇怪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评论,有人就高度评价贝多芬“给黑暗带来光明,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深刻与和谐的气质”,并且称赞《第三交响曲》是“迄今为止,贝多芬以其卓异的创造力所作的最广博、最天才的作品!”
《埃格蒙特序曲》是为歌德同名悲剧而写的戏剧配乐,也是应宫廷城堡剧院(Hofburgtheater)艺术指导的委托而作,这位仁兄打算排演歌德的《埃格蒙特》和席勒的《威廉•退尔》。据车尔尼的说法,贝多芬主要是对《威廉•退尔》感兴趣,只是《威廉•退尔》已经交由维也纳的作曲家阿达贝特•基洛韦茨去完成。贝多芬在1810年8月21日的一封信中提及他创作《埃格蒙特序曲》是出于“对诗人的爱戴”,他还把他的手稿送给歌德,在附信中他写道“……这精彩的埃格蒙特,我第一次拜读,我用同您火热的眼神一般的热情,来创造这首曲子——我期盼着您的观感……”(1811年4月12日),歌德有礼貌地予以回应。1810年7月15日,《埃格蒙特》第一次作为贝多芬的音乐首演。安东尼•安达尔伯格(Antonie Adamberger)(莫扎特《后宫诱逃》中贝尔门特扮演者的女儿)担任克雷馨一角。序曲并没有概括全部剧情,但却准确地把握了歌德作品的精髓。肃穆的开头采用的是阴郁、压抑的f小调(和《费德里奥》地牢一场的调式相同),它的主题沉重感人,将听众带入充满冲突和痛苦的英雄的世界。主要主题是快速的3/4拍,炽烈如火,结构显示出的方向感十分鲜明,以至于贝多芬不用去操心戏剧中的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人物:呈示部、短小的展开部,再现部组成的音乐构架具有叙事曲的全部特点,戏剧冲突发生在快板的结尾,不屈不挠的冷酷下顿的动机(和乐曲开头的持续音型很相似)成为猝然终止的前导,由ppp的力度标记进入活泼、朝气蓬勃的快板(allegro con brio),这个F大调的狂放的凯旋进行曲已经预示了戏剧配乐结尾的“胜利进行曲”。也许人们很难接受E.T.A.霍夫曼在1813年对贝多芬《埃格蒙特序曲》的著名评论,他认为该曲表现了埃格蒙特和克雷馨的爱情,但人们不能不同意他所说的,“看到两位伟大的艺术家联袂合作的杰出作品,真是人生一大乐趣啊。”
《第四交响曲》
在19世纪末期,贝多芬《第四交响曲》也许是他所有交响曲中最不为人知的作品了,因为乐曲缺乏故事情节和英雄人物。瓦格纳曾认为它是“平淡无奇的音乐”,虽然他承认其中的谐谑曲很精彩。柏辽兹(Berlioz)的评论则更为深入,他说贝多芬“抛弃了一切浮华的赞美和娇柔的挽歌……只是为了回归《第二交响曲》那种少许庄严,少许激烈,但并不简单的曲风之中。《第四交响曲》展示给我们的形象是生动的,清新的,具有尊贵且神圣的精巧……”实际上,在《英雄交响曲》之后,贝多芬《第四交响曲》(作于1806年)是又一部超凡脱俗的作品,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散发着宁静的气息,仿佛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来俯瞰世界。每个小节都是它的作者内心世界的写照,贝多芬在这部作品里回归到海顿的创作精神(就像他在《第八交响曲》中表现的那样)。事实上,海顿比莫扎特更能启发贝多芬的灵感。他请到了曾为海顿和莫扎特演奏过的交响乐团:为了更突出地表现乐曲的空灵,他甚至去掉了长笛的第二声部。正是乐曲所营造的飘渺气氛,使得舒曼称它为“希腊的苗条女子”。然而交响乐团所奏的每个音符又都完美契合了贝多芬的特征,这是乐曲最让人惊叹的地方之一。《第四交响曲》的长度与第一和第二交响曲相当。乐曲以缓慢的引子开头,就像多数海顿的晚期交响乐作品和贝多芬自己的《第七交响曲》那样。这份量十足又广阔无边的柔板从一开始就证明,这部作品无论是其对美的渴望还是已经展现的美感,都毫不逊色于其他的佳作。除去少数几个重音,整个引子都是轻柔的或者极弱的。在三个和弦的间隙,一个大的渐强将整个旋律推向了最强音,使得柔板随着情绪的苏醒而生机勃勃。在这样的手法之下,整个交响乐的主体被极其准确而简明地引导出来。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感受到了乐曲中那难以平息的强大的导向性意念。乐句发起的迂回能量被一段可塑性极强的自由演奏加以延续。乐章的展开部短的不同寻常。在贝多芬的作品中,这部分通常是展示乐曲最精彩片段的部分,但在这部交响曲中,它却留给了我们不同的印象。第一支主旋律——一个下行音程的颤音(八分音符),在实际展开过程中逐渐变得舞蹈般轻盈,特别是当一丝音调优美的飘动线条(首先在小提琴和大提琴的旋律中听到)像守护天使一般围绕着它时,又如线条在主旋律的五次反复中穿越一个又一个的和弦之时。第二支主旋律透过低音管、双簧管和长笛的演绎(从107小节开始,起初是F大调),营造出一种浓重的田园氛围。第一乐章柔板中那浑然天成的纯粹欢愉,在律动的休止符向悠扬如歌的对位转化过程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第三乐章(活泼的快板:全乐章均为诙谐曲)由节奏错综复杂的变化逐渐过渡为一派庄严的平静。交响曲的末乐章仿佛一场喧豗的舞会,一面是欢乐嬉戏的音符,一面跳跃着极富创造性的灵感。这个乐章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因为它并不像贝多芬其他的末乐章那样庄重,有英雄般壮烈的色彩,但它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无穷动(perpetuum mobile)的跳跃节奏中交织了从容的优雅和机敏的智慧。
尽管贝多芬《第四交响曲》在结构上清晰明了,但许多与贝多芬同时代的人并不认为它相比于贝多芬其他的作品,更容易理解。贝多芬《第四交响曲》的首演(半公开)是于1807年3月在利赫诺夫斯基的宫殿举行的,坐在台下的是一批“精挑细选的观众”。克茨伯尔(Kotzebue)在他的杂志《Der Freimutige》中写到“贝多芬又写了一部大概只有他最狂热的追随者才会喜欢的新交响曲”(1808年1月14日)。而后卡尔•马尼亚•冯•威伯的尖刻评论,也暗示了贝多芬的音乐即将脱离传统,开创一个新的浪漫主义时代。
《第五交响曲》
《第五交响曲》是贝多芬最短小的交响曲之一,并不比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和海顿的“伦敦交响曲”来得长,然而它的创作过程并不简单,作品完成于1808年春,而手稿的时间跨越1804至1806年,写作过程并不是连续的,曾一度被一系列重量级作品的创作打断,这些作品包括《G大调钢琴协奏曲》,《第四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在1807年,贝多芬同时着手创作第五和第六“田园”交响曲,后者紧随《第五交响曲》之后完成。而后,听众们便见证了创造力量的汇聚:在1808年12月22号的维也纳剧院的历史性音乐会上,他开出如下的节目单,都是自己从未上演过的全新作品,它们包括《音乐会咏叹调“啊!不忠实的”》、《C大调弥撒(op.86)》的若干乐章,《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作曲家担任独奏),《第五交响曲》(标为第六交响曲)(在公告中,“田园”交响曲的标题误置于《第五交响曲》之上),钢琴即席创作以及《合唱幻想曲》op.80等。随后的报纸称:“对于这场音乐会的方方面面,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不能令人满足。”仅仅是贝多芬的即兴演奏和钢琴上的演奏被认为接近他平常的高水准。
《第五交响曲》的独特与革新的品质在第一乐章表现得尤其显著。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的相反一极,不是因为“命运的敲门声”(这是贝多芬对他的助手和第一个传记作者辛德勒所说的),而是因为他大胆起用一个单一主题——四个音符的短小动机——由此构筑大尺度的交响曲乐章,其重要特征就是不同种类材料的自由结合。如果说《英雄交响曲》的使命是通过不同的多样性元素去建造一个坚实的、连贯的建筑结构,《第五交响曲》则是从同一中产生出多样性,一些习见的技巧被废弃不用,主要动机的结合体(分为两个下行的三度音程)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对于交响曲的写作,这是全新的。基本主题作为一个动机,不仅浓缩了一个乐章,并且有一股对于联接终极目标的不屈不挠的性格,而且这个性格已经内在于基本主题了。《第三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并且,它是C小调,正好是降E大调(第三“英雄”交响曲的调性)的关系小调。同时,它也可以使用“英雄”这个标题,在这首交响曲中,英雄意志的展示并不弱于《第三交响曲》。
《第六交响曲》
《第六(田园)交响曲》和伴随着它的《第五交响曲》存在相似之点,虽然它们基本性格的差异之大,已经到了无法比较的地步。《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基本主题又一次包含了“敲门”动机,一个弱拍引入一个有力的强拍。在《第五交响曲》中,第三乐章与容光焕发的C大调终曲之间的联系已经预示了《田园交响曲》乐章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五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最初被设想为一个孤立的乐章,是后来才与终曲乐章联系在一起的。挽歌一般,然而坚毅的第二乐章(降A大调生动的行板)是一个变奏曲,具有不寻常的结构,实际上包含了终曲的C大调号角的一次陈述,这引起了很多注释者的猜疑,他们推测这两个乐章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个假定的进程——“通过斗争和苦难走向胜利”——是一个不合适的公式,其实除了狂欢的终曲乐章之外,并不存在支持这个公式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欢乐与和解是交响曲末乐章的普遍特征——在海顿和莫扎特的交响曲中也是如此。《第五交响曲》的结构显示了明确的意图,这必定会加深一种错误的信念,那就是这部作品也可以当成一个“故事”来讲述。想象的主体和客观化的情感被贝多芬熔铸为一个结构,这结构却被误认为是由一个主观化的“我”创造出来的。贝多芬的音乐不需要用任何个人经历过的感情或者冲突来加以图解,也不需要叙述由独立的音乐形象联想到的事件。《第五交响曲》的统一性不存在于“诗意”的安排中,而存在于它的内在的音乐性的关系之中。
对自然的描绘是十八世纪音乐的一个普遍特征。表现雷声尤其盛行,这是艺术中的田园诗传统的回归:牧羊人的生活被认为象征着世俗的欢乐,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田园牧歌的理想。这是贝多芬《第六交响曲》所属的传统。F大调这个调性一直代表着田园诗,代表着田园牧歌,贝多芬并没有致力于对自然现象的现实主义图解,不妨说,大自然被一个敏感多情的旁观者的情感浸透了。考虑到他的作品可能会被误解为音画或程序化的音乐,贝多芬特别为他的作品加了一个完整的标题:“田园交响曲,或者是对乡村生活的追忆(写情多于写景)”
在贝多芬的时代,已经存在足够多的仅仅表现风景或事件的作品。贝多芬希望自己和陈腐的音画脱离关系,因为这类作品获得的尊重是比较少的。比如歌德在给他的朋友作曲家策尔特(Zelter)的信中说:“用声音描绘声音——打雷声、撞击声、泼水声、击水声——是叫人讨厌的。”
在一定程度上,贝多芬的同时代人已经理解“田园”并不是简单模仿自然界的某个场景,而是通过音乐这一媒介诠释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贝多芬伟大深切的对于自然的热爱是这部作品的基础(他说过,我爱一棵树胜过爱一个人),但这种爱不同于浪漫主义的schwÄrmerei(狂热),在1816年的札记里,贝多芬借康德的一句话,将他的自然观表达得非常清楚,“如果世界的构造反映出了秩序和美,那么定然是有一位上帝了。”这就是“田园”的自然神学吗?当然不是,但是毫无疑问,音乐表达了一种客体的可能性和假定的人与自然的无条件和谐。
自然的描绘仅见于第二和第四乐章。第一乐章并不是一幅风景画,而是一种情绪的音乐表达,这种情绪是在对惬意的乡村生活的期待中生发出来的,如果整部作品是一次“追忆”,是呈现保留在记忆中的意象的话,那么,第一乐章就是走进被自然浸透了的意象世界的入口。在作品的中心——“溪边景色”里,自然具有纯然独立的性质,仅仅反映在善感的人的情感中。谐谑曲似的第三乐章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相反一极,人在自然中汲取力量,自然带给他安宁与和谐,个人在舞蹈中忘记了他的忧愁,这是全曲中,人的场景的第一次出现。但当大自然释放其力量的时候,他还将感受到自然的威力:舞蹈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断,人意识到他的脆弱。第四乐章一定是交响性结构中的一个异质的部分,表现了大自然在发挥其力量时,超越人类感情控制的基本的、破坏性的方面。可以说,这是全曲唯一一个可以找到声音描绘的乐章。仅仅是在最后乐章,贝多芬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体验到对于自然的敬畏,意识到人的脆弱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几乎具有无限深度的概念。暴风雨之后的感恩颂歌是对和解和快乐的庄严表达,这个乐章对音乐发展的轮廓提供了一个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贝多芬要把最后三个乐章联成一体,同时,每个部分都是其他部分的条件,它们内在的互相包含在一起。在《第五交响曲》中,善感的、主观的心灵发出了不可征服的、英雄般的力量,以及对于创造世界的崇高想象。在《“田园”交响曲》中,同是一个主观的心灵,其想象力黯淡下来,在沉思的氛围中,遭遇到了另一股力量,这力量在自然的观念中被铭刻在心。
《第七交响曲》
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是题献给他的赞助人莫里茨•冯•弗里斯(Moritz von Fries)的,他是一位银行家和艺术赞助人。在1815年6月1日致约翰•彼得•萨勒曼(Johann Peter Salomon)的信中,贝多芬称这部作品是“我最好的一首交响曲之一”。其实他何尝不可以对他的每一部交响曲都这么说呢?不过,他这么评价《第七交响曲》是不难理解的,我们考虑到贝多芬度过了在他的生涯中极其重要而多产的四个年头——从《田园交响曲》(1807-08)至《第七交响曲》(1811-12)刚好是四年,这是他创作一系列交响曲过程中一个最长的间歇。也可能是他没有忘记《第七交响曲》在重要的大学音乐会首演时得到的热烈欢迎(1813年12月8日)。这场音乐会是为汉诺威战役中的伤员举行的义演,同时为庆祝拿破仑在西班牙的败北,贝多芬的《威灵顿的胜利》(又名战争交响曲)也是因纪念此事而作。维也纳公众能欣赏这部作品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在其他的城市,听众对于交响曲冷冰冰的节奏感到不安,莱比锡首演之后,就有人议论,贝多芬一定是在酩酊大醉时写的第一和第四乐章,而威伯更断言:贝多芬已经“可以进疯人院了”。
毋庸置疑,《第七交响曲》会让第一次听到它的人们感到诧异,第一乐章起始处的引子,无论长度和分量都超过了《第四交响曲》以及此前的任何一部交响曲,对于初听的人们,需要一种特别的把握有分歧的结构关系的能力,并保证自己在这个一再拖延的引子中不迷失方向,这个引子热忱地朝着一个目标挺行,不断产生新的开端,直到管乐的旋律进入。在本体(Vivace)进入之前,整体的逻辑上的删减也是令人惊讶的:回归充满活力的E大调(概括了主体的节奏基础)。快速的乐章主体出现,引子的沉重感被一扫而空,其基本节奏和主要主题丰富的抑扬顿挫充满了芭蕾式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中,音乐宣告了它所获得的新的自由。贝多芬在贯穿整个乐章的基本节奏型之下,展开动机和结构多样性的手法是他的又一创举。最后,贝多芬借开头主题的音符和低音部的固定音型结束这个乐章。瓦格纳后来每每称引的“舞蹈的颂赞”主要是就这个乐章而言的。
这部作品在维也纳上演之初,第二乐章快板乐章总要应要求重奏一遍,并且很快成为贝多芬交响曲中最流行的篇章之一,整齐划一、进行曲般的律动显示的一个无处不在的节奏型统治了整个乐章,让听众想到行进着的队伍。进行曲的律动与教堂会众的祷文颂唱有一种联系,在这方面,贝多芬的同时代人阿贝•斯特勒值得一提,他在第三乐章(标为急板)三声中部的主题中发现了朝圣者的赞美歌。队伍在一系列的变奏中前行,尽管居于主导地位的A小调弥漫着哀愁的气氛,但还是有两个A大调的插段,带来些许安慰,其旋律很像《费德里奥》第二幕中弗洛伦斯坦的“在更好的世界里愿你得到回报”(euch werde lohn in bessern
welten),这应该不是偶然的,贝多芬的助手,也是他的第一个传记的作者安东•辛德勒一定知道作曲家的意图,他称这个段落为“安慰性的大调段落”,据他的说法,贝多芬希望它在速度上可以“更加清新、更加活泼,更有朝气”。此外,这个乐章在整体上更接近行板的性格,比所标示的“快板”更加安静,尽管天堂的大门仿佛打开了,但乐章开头和结尾都采取了奇怪的悬而未决的手法,在第二转位时带着一个小调的分离的和弦,为不和谐的音调增加了几许辛辣的味道。快板的哀伤不久就被第三乐章的急板冲散了,这是一个心醉神迷的舞曲乐章,在D大调三声中部中,有一个安详的A大调插段。末乐章基本的、回旋式的动机(其节奏音型可以看作第一乐章带附点的节奏型的变异)来自爱尔兰民歌《把我从坟墓中解救出来》的曲调,贝多芬曾经改编过这首民歌,并为它写了钢琴伴奏,如果当他写末乐章时考虑到了这首民歌的话,那么把这个乐章解释为一种释放的行动未必不是恰当的,难道在这个末乐章中,还能找到比这更崇高的理念吗?
《第八交响曲》与《莱奥诺拉》序曲
贝多芬的《F大调第八交响曲》于1817年首次发行。与它相临的《第七交响曲》相比,贝多芬称它是一部“小型”作品。然而这样称呼它仅仅是因为乐曲长度较短,其艺术价值还是不容质疑的。这部交响曲的创作仅用了1812年夏天一段相当短的时间。透过贝多芬的手稿我们可以发现他是如何精心创作和细致雕琢这部作品的,以第一乐章为例,其尾声在原基础上加入了34个小节的扩展丰富,但在1814年2月27日维也纳Grosser Redoutensaal 音乐厅进行的首演中,也许并没有演奏这些补充的部分。除了他的歌剧《莱奥诺拉》将已完成的作品进行补充之外,这样的工作对贝多芬来说并不多见。像创作《第四交响曲》那样,他徜徉的思绪,他明确的、独特个性的完整保留,使他又回到了对古典交响曲中那原始结构的追求,传承着海顿的精神。比如,他首先使谐谑曲乐章从自己创造的曲风中脱离开来,又回到了传统的“小步舞曲”(虽然他早在《第一交响曲》中就将“小步舞曲”加速成了“优雅的小快板”)。在此,他既展示了对传统曲式无以比拟的继承,又表现了他独具匠心的创造。
第一乐章(非常生动的快板)的开头没有采用任何刻意吸引观众注意的手法:包括加入缓慢的引子,使用中心旋律或者尖锐的和弦。相反,乐曲开门见山,立刻就向我们呈现了乐章主体,特征鲜明,极富动感,简洁明了。然后,贝多芬好象又要迫使自己打破这个主体,他使乐曲充分展开并赋予其丰富变化,从而透过这两小节的主旋律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贝多芬采用了特别的节奏和类似一连串韵律诗的手法。音乐在进行到标有三个强音记号的再现部,以及主题以新的形式呈现时,达到了最高潮。但实际上直到乐章尾声(同样标有三个强音记号)我们才能体会到乐曲到了决定性的收束。尾声中末12小节突然降至弱拍,在最后两小节又减至极弱,机智地展现了诗一般的韵律。根据贝多芬给他朋友梅尔策尔(Johann Nepomuk Malzel)所写信件的描述,接下去第二乐章谐趣的小快板,依旧延续了前面诗般的韵律。梅尔策尔是节拍器的发明者,因此贝多芬写到:“Ta ta ta…lieber Malzel,leben Sie wohl,sehr wohl! Banner der Zeit,grosser Metronom…”(嗒 嗒 嗒……我亲爱的梅尔策尔,再见了!时间修理者,那伟大的节拍器……)柏辽兹(Belioz)评价这个乐章是“找不到模式的,绝无仅有的,浑然天成的……我们聆听时都被它震惊了……”。在第三乐章小步舞曲中,贝多芬似乎要向我们证明,即使是采用最传统的优美的兰德勒舞曲*,也能够表现高雅艺术,末尾部分木管乐器突然出现,是这个乐章最有趣的地方。终曲活泼的快板当属贝多芬最复杂、巧妙的末乐章之一了。柏辽兹非常欣赏它的“生机勃发”,认为乐章的主题“卓越非凡,新颖奇特,最大限度地展示自身”,而这个乐章主要的乐思其实是第二乐章主题的精彩重塑。
《第八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时,得到的评价远没有不久前公演的《第七交响曲》那样高。据车尔尼说,贝多芬为此感到很不快,“因为他认为《第八交响曲》要远比《第七交响曲》优秀”。最不公平的是,即使19世纪时人们的欣赏口味已发生改变,《第八交响曲》仍然被贝多芬其他著名交响曲的光芒所掩盖。瓦格纳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并未注意到《第八交响曲》的优秀,认为它是“冷门音乐”。
贝多芬为歌剧《莱奥诺拉》写了不下三首序曲,这也印证了贝多芬最感兴趣的一个想法:将戏剧中概念性的内容用一种自然形成的同时又极具说服力的音乐片段表达出来。正因为如此,他于1807年创作的《柯里奥兰序曲》被看作是一部独立的作品,即使它原本是为他朋友海因里希•约瑟夫•冯•柯林(Heinrich Joseph von Collin)的著名悲剧《柯兰奥拉》(1802)而作。柯林(1771-1811)当时是维也纳的著名剧作家,而且莫扎特的妹夫约瑟夫•朗格(Joseph Lange)在剧中饰演主角,因此贝多芬想当然地认为序曲的听众应该都知道那部悲剧。序曲于1807年3月在拉克维茨(Palais Lovkowitz)的一场联票音乐会上首次公演,而后又在4月24日戏剧的重演中再次奏响。这个序曲与贝多芬以往的作品有相当大的反差,“为戏剧而作”似乎成了一个借口。作品以它的激情与力量在问世之后立刻得到热烈反响。作家兼作曲家霍夫曼(E.T.A.Hoffmann)在1812年发表的一篇热情洋溢的公告中评论到,“音乐的内容远比戏剧本身出色。震撼性的开头将悲剧性格清楚地揭示出来,虽然乍听上去它与作品的整体节奏(生动的快板)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贝多芬选择c小调来创作并不是偶然的,他依照自己的理解谱写出极具个性的乐曲主题:一个是生动有力,另一个则呈现出理想的梦幻世界的美感。贝多芬仅用“极其简单的材料”就修筑了“一个精妙绝伦的建筑”(E.T.A.Hoffmann),任何乐曲背后的舞台表演对于乐曲的理解都是多余的。《C大调第三号莱奥诺拉序曲》是为了歌剧《费德里奥》(1806年3月29日)的重演而作,重演在原版本基础上进行了删减。(《第一号莱奥诺拉序曲》作于1806-1807年间。《第二号莱奥诺拉序曲》作于1804-1805年间,是歌剧的最原始版本,于1805年以莱奥诺拉这个名字首演)。第三号序曲是贝多芬所有序曲中当之无愧的最重量级作品,其内涵是最丰富的。贝多芬先前创作的序曲受到了很多犀利的批评,这促使贝多芬不得不重新审视他的创作观。实际上这部序曲同样得到了负面的评论:“不和谐音符不断地冒出来,小提琴总在演奏那累赘的弓法,像在炫耀技巧而不是展现真正的艺术……”(《第一世界报》(Zeitung fur die elegante Welt))。作品的确以这种方式展示了序曲的框架,一部歌剧的序曲框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歌剧最初起源于德国的歌唱剧(Singspiel)。与第二号序曲以及后来的第一号序曲相同,《第三号莱奥诺拉序曲》也兼顾到了戏剧的情节。在开头那宽广无际的柔板里,音乐逐渐淡去,就像跌进了弗洛斯坦阴森黑暗的囚室,直到他的叹咏调响起(“In des Lebens Fruhlingstagen”)。在柔板中,音乐发展到最强劲猛烈的时刻——这通常是乐曲的关键一刻——我们听到了从远方传来的坚毅呼声,预示着自由即将降临。在《第二号莱奥诺拉序曲》中,贝多芬根据戏剧的逻辑需要,为这段音乐续上了一个欢天喜地庆祝胜利的急板。在第三号序曲中,在最终回到急板之前,贝多芬加入了一段意味深长的主题重现,对乐曲进行了扩充。然而瓦格纳却认为这处理与实际的故事情节相违背,与《第二号莱奥诺拉序曲》相比,这是个败笔。其实贝多芬考虑的是怎样用音乐对戏剧的思想加以独特的理解,并将其真实有力地表达出来,而不仅仅对舞台表演机械地照本宣科。最终敲定的歌剧《费德里奥》1814年版,已不再以玛泽琳娜(Marzelline)的c小调叹咏调开头,取而代之的是一段A大调的二重唱,这使得贝多芬不得不重新为它谱写一个序曲。这个所谓的《E大调费德里奥序曲》在歌剧第三版(即现在所说的《费德里奥》)的首演上并没有出现,而是在3天后(1814年5月26日)的第二次演出中才与观众见面。在这个序曲里,贝多芬并没有刻意突出其与歌剧的联系,但是我们很难再列举出一部如此优秀的作品:冒着受到观众批评的危险,尽力使歌剧的主题透过音乐得以升华。
《第九交响曲》
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惊人的创作,在交响曲的历史上,它第一次冲决了器乐音乐的边界,这在很早的时候就引起争议,威尔第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满怀敬意,却对末乐章感到困惑,考虑到贝多芬多么无情地对待声乐,倒也不难理解。对于瓦格纳,则在这里找到了艺术上的授权——来自最高的,可以想得到的权威,从而得到他的命题,那就是诗句可以对音乐作出补偿,而贝多芬自己则已经推开了通向音乐新时代的大门,一脚踏进音乐戏剧的时代。
不过对于末乐章发生异议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搞乱了“绝对音乐”和“自为音乐”的区别,并且拒绝承认这个庞大的变奏曲乐章能够与任何莫扎特的叹咏调或者终曲相提并论。对于作品的不满和作品本身一样古老,并让人们对贝多芬后期作品的困惑有增无减,至少这是我们读到的情况。然而,在贝多芬的时代,也有令人吃惊的对于这部作品的正面评论,比如伊格纳茨•冯•谢尔弗里德(Ignaz von Seyfried)的评论,顺便提一句,他是贝多芬的私人朋友,在一篇1828年的文章中,他称《第九交响曲》“在材料的广度和多样性,以及精神上的苦心经营都超出了此前所有的作品,”关于末乐章,是“真正的杰作,无愧于作者的名字”,尽管“有一点可以确定,贝多芬如果听从朋友们善意的,可信赖的建议,并像他在后期四重奏中做得那样,这部作品一定可以更合乎目的(比如OP.130,原来的末乐章就是后来的《大赋格》op.133)
为使这部宏伟的创作和此前的作品一样易于上演,当大型合唱队与可靠的独唱者找不到的时候,人们是可以自由选择终曲乐章形式的(采用声乐或者器乐),其实贝多芬原本也可以这样做,而他在创作中途也有过犹豫的时刻,毕竟,他原来的计划是写一个纯器乐终曲的,终曲乐章的初稿采用的就是A小调弦乐四重奏(op.132)的主题,这在今天创作交响曲的语境下是不能想象的。同时,不应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对席勒的存在,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合唱交响曲》的终曲有一个远祖,那就是1808年的《合唱幻想曲——为钢琴、合唱与乐队而作,op.80》。实际上,这部作品通常被认为是贝多芬不太成功的作品,但当贝多芬将《第九交响曲》总谱交给莱比锡的出版商普罗布斯特(Probst)的时候,提到,“同类的创作是我的钢琴、乐队幻想曲,只是现在这部作品具有更大的广度”(1824年2月25日),可见,《第九交响曲》并非凭空出现。据卡尔•车尔尼的说法,在《第九交响曲》首演之后,贝多芬向少数朋友表示过终曲是一个错误。并打算用一个纯器乐乐章取而代之。我们没有必要考虑车尔尼作为一个当事人的可靠性,也不去考虑假定贝多芬真的这样说了,其用意何在。只是可以看出,车尔尼用来支持其观点的热情看起来是多么大啊。
再来考察一下《第九交响曲》末乐章的缘起,早在贝多芬写《合唱幻想曲》之前,席勒的颂歌《致欢乐》已出版于1786年的期刊《塔利亚》,同时发表的还有几首席勒的其他诗歌。当贝多芬将诗歌纳入交响曲的时候,他采用的是这首颂诗较后的版本。早在波恩时期,贝多芬就已经被这首诗歌吸引,1793年1月26日,未来的政府议员费歇尼希(Fischenich)(年轻的贝多芬经常造访他的住处)在写给席勒妻子的书信中,提到贝多芬想“给席勒的《致欢乐》的每一句都谱上曲子,我期待他能完美地做到这一点,因为据我所知,他可以做到崇高和庄严。”
费歇尼希一定意识到席勒诗篇中的崇高意念会拨动贝多芬的心弦,颂歌一定会让他激动,其实,在贝多芬1798年的手稿中就有下面的话:“muss ein lieber vater wohnen”(慈爱的父一定存在)。 对于《第九交响曲》终曲合唱最重要的过渡性的一步,就是《费德里奥》(1804-5,1805-6,1814年)了,这部歌剧改编自德国歌唱剧(Singspiel)。无疑的,席勒的诗句(wer ein holdes weib errungen,stimm in unsern jubel ein)出现在《费德里奥》终场是贝多芬的意愿。如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那样,诗句的格调保留得很完整,但两部作品表达的并不是相同的东西。绝对无条件的理想主义和解在这世上可能实现吗?我们在歌剧的结尾,当主人公个人的命运对于他们支持的东西(人类在爱中结合起来)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理想的实现。在席勒的第一个版本中,附带说一下,诗句的力量较弱,也不是那样具有普遍性(原文作:“乞丐将成为公侯的兄弟”。)在1811年,贝多芬用C大调为席勒的诗歌谱了曲,增加了下面的句子,“freude schone gotterfunken ,tochter”。并写出了序曲——“欢乐,带来了神的光芒,极乐世界的女儿”,此外,还有不连贯的句子,比如:“公侯就是乞丐”——席勒的欢乐颂中的分离的诗句被结合成了一个整体。
我们已无从知道贝多芬是否只是想创作一个序曲(一个包含合唱的非凡序曲)或是一个由序曲引导的合唱作品。关于将诗句运用到《第九交响曲》末乐章的想法,贝多芬在他1822年的札记中第一次提到:“Sinfonie allemand (德语交响曲),或者在唱完‘Freude, schooner Gotterfunken’(欢乐女神圣洁美丽)后引入变奏……或者不引入。交响曲的末尾要加入一段土耳其音乐和合唱。”其基本构想已在此时形成:采用合唱以及席勒的诗,还有变奏曲的曲式以及土耳其音乐。
《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是威玛古典主义与维也纳古典主义的首次交汇,流露了作曲家对音乐艺术至高无上的追求。这次交汇的深远意义远不在于重要作曲家采用了重要诗篇,而在于贝多芬与席勒的精神中那股亲和力。他们不约而同地崇尚一种精神上的理想主义,即人实际是由人类庄严的意志所塑造的,虽然他们身边的许多事例证明人也有懦弱的时候。除去一切集中或分散的内容形式,到底席勒的颂词与贝多芬的音乐还有什么是融合在一起的?答案当然就是那个尚未形成具体实物的领域,既不是音乐,也不是词汇。当我们不禁疑惑,贝多芬的音乐是否能将诗的意境完整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席勒诗中还蕴涵着虔诚祈祷的和谐旋律以及激扬人生的灿烂音符。贝多芬的音乐和席勒的诗被认为是异曲同工,甚至贝多芬从不介意人们将音乐与文字原版做比较。虽然贝多芬对歌德和席勒怀着深深的敬意,但在音乐方面他是主人,有权根据旋律的走向来修改诗句。诗原本包含9个主体部分(每部分8行,韵律是ababcdcd),9个齐唱部分(每部分4行,韵律是abba),一般情况下预示着齐唱与独唱的转换,但有时视具体内容而定。然而贝多芬并没有采用席勒提出的主体与齐唱简单轮换的建议,而是根据自己对音乐的理解重新组织了诗句。他将席勒诗的前三句(”Freude,schooner Gotterfunken…”;”Wem der grosse Wurf gelungen…”;”Freude trinken alle Wesen…”)原封不动地放在了乐曲的开头。然后他将诗里的第四个合唱部分作为了乐曲里的第一个,紧接着又是第一主体的重复(”Freude,schooner Gotterfunken…”),但这个主体之后是诗里的第一和第三个合唱部分(”Seid umschlungen, Millionen…”;”Ihr sturzt nieder, Millionen…”)。接下去的部分他结合了诗中第一主体的前4行以及第一合唱部分(”Seid umschlungen…”),作品以开头的祈愿语句结尾:”Freude, schooner Gotterfunken”。
说《第九交响曲》是席勒诗的配乐是不准确的。乐曲并没有照搬原诗,就像贝多芬自己描述的那样,这个作品是由诗中摘出的单独句子重新组合而成的。为了避免诗句在乐曲中有任何的逊色,贝多芬将它当作歌剧的台词一样使用。不论是诗句的选择和重新组合,还是整个乐章错综复杂的编排,都只能在听完整个乐章之后在乐章整体中加以理解。减弱或者淡化乐曲固有结构的举动是无可厚非的。贝多芬构想了一个伟大的变奏计划:交响曲的结构原则自然让他考虑在器乐上进行变奏,就像《英雄交响曲》末乐章呈现的那样。《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以三段纯器乐变奏开篇,后以尾声强调了乐章的自由结构。席勒的诗和变奏规则之间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尽管后者在我们看来显然是独立的。席勒的颂诗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能够将全人类召唤在一起迎接欢乐,而在贝多芬的变奏中,前后是两段较平静的旋律,将我们引向超脱与永恒(庄严的行板:”Seid umschlungen, Millionen…” 以及不太快的柔板:”Ihr sturzt nieder, Millionen…”),变奏部分则使我们无一例外地陶醉在舞蹈之中,伴随着音乐的节拍越来越尽兴。 席勒的诗歌服从了器乐,特别是交响乐末乐章的理想,从本质上来说,它表达了对立面之间的调和,矛盾在欢乐中得以化解,障碍得以消除。器乐与声乐的结合逼真地显示了人类社会各等级的和解。全人类聚集成一个自由欢乐的大家庭。这个主题时刻回荡在贝多芬笔下的音符之中,这就是贝多芬和席勒的思想交汇之处。
还有两个疑问有待解答:《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乐章是怎样与前个三乐章交相辉映,使全曲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的呢?还有,这个乐章究竟采用了怎样的形式去配合席勒的诗句?在《第九交响曲》中,谐谑曲出人意料地成为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从而使前两个乐章平稳地过渡到了缓慢的第三乐章直至最后乐章。从某种角度去欣赏,我们很容易将第二乐章联想成是第一乐章的结局,一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的热烈狂欢在此渐行渐远。而《第九交响曲》中间那平静流淌的柔板,以娓娓道来的变奏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趋向末乐章。全曲平静的中心——第三乐章以变奏的形式表明了它与第四乐章的亲缘关系,但这两个变奏曲乐章并不能视同一律,在第三乐章柔板展开的过程中,变奏带领主题逐渐回复,聚敛,音符指引我们步入深思和冥想。而第四乐章的变奏却走出沉思,去开辟崭新的境界。
贝多芬最初仅为席勒的诗写了一段《欢乐颂》主旋律,其后的变奏都是围绕这个主旋律展开的。这是一串令人惊叹,振奋人心的音符,承载着超越音乐本身的高贵情感。从它自身迸发力量,再次彰显了那个古老的美学标签:“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主旋律的合唱部分犹如虹桥般壮阔,音符在桥下无拘无束地自然流淌,是那么清晰地被感知,却又那么平静。在《欢乐颂》的主旋律里,最伟大的艺术正是通过最简单的方式得以表达的(我们可以从贝多芬多次修改的手稿中看出他为创作这段旋律付出了多少汗水)。这是一件纯粹的艺术杰作,无视一切等级贵贱,是人性的复归,是走向理想世界的坚定信念。这样的音乐将生机与欢乐撒向人间,谁又能说这样的主题违背了席勒的原意?他将他憧憬的幸福灌以躯体与生命,使之与人性紧紧相拥,这旋律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声讨了社会里的不公正与不平等,摈弃了生活的诸多限制。它号召我们追求自由,心怀尊严,从而使社会更加高尚,世界更加美好。实际上,音乐的内涵与诗词的思想是殊途同归的。我们同样可以明白地看到,席勒的诗——以第一个主体为例——在旋律中以最简易的方式清楚地呈现,并与长为16小节的主旋律完美契合。主旋律由4个部分构成,每部分的4个小节都对应了两行诗句;凭借旋律后两部分的重复,贝多芬将整个乐句扩充为24小节,而重复部分与诗的第二主体(”Deine Zauber…”)对应。同时,贝多芬的旋律在尽量反映原诗思想的基础上,也表达出了比“欢乐”个词本身更深远的意义。因为乐曲首先呈现给我们的并不是铺天盖地的欢腾或喜悦,而是轻柔、反思、平和的气氛。我们在第二主体中更能看到语言与旋律之间的默契,它展示给我们的欢乐能聚集力量,战胜分裂,让所有人在它的庇护下亲如一家。《欢乐颂》主旋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广泛的包容性,它那团结一切力量的不可阻挡的势头,它是变奏中展现的精彩纷呈的欢欣愉悦的根本基础。
厦门吉他网
厦门吉他培训中心
|